
從涇渭分明到殊途同歸─談法官與學者的角色侷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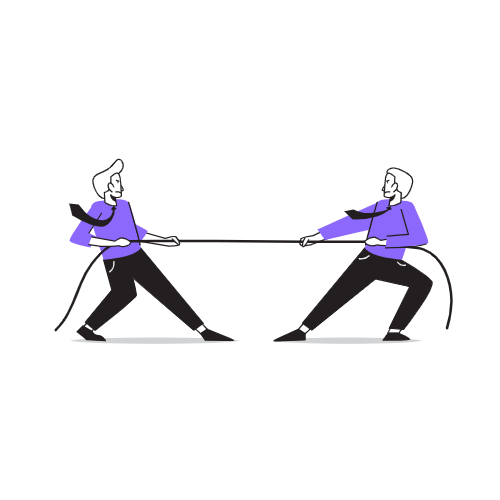
司法權是國家權力的態樣,其與行政權、立法權的明顯區別在於:司法權的效力全然仰賴「判決理由」。如果捨棄「判決理由」,司法判決即毫無影響力1。「判決理由」是法官思想、智慧、經驗的結晶,具有賦予國家權力作用的效果,所以法官的地位被視同祭司(oracles)、先知(prophets)和哲人2(sages),也是其來有自。
在法律專業領域,除了法官之外,學者對於法律詮釋和理論發展同樣具有重要影響。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雖然都以專業菁英自詡,但是兩者功能不同,因此存有差異不僅理所當然,而且中外咸同。
首先:法官解釋法律必須受限於法律規範,但是學者基於學術自由勇於創設理論,並對不符合其理論的法律規範採取輕忽或無視態度。因此產生的現象就是:學者創設的理論越前衛,能夠作為裁判理由的有效性就越低3。
其次,除了研究法律的基本態度不同,法官和學者對於彼此專業產出的成果(即判決和論文),相互的評價也是針鋒相對。法官抱怨學者的論述過度鋪陳,空泛援引不具直接相關的文獻4;學者則批評法官的理由簡化跳躍,迴避重要的法律爭點5。
例如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法官Harry T. Edwards即曾嚴詞批評美國的法律菁英名校,放棄適切的角色,犧牲法律實務的教學方法,反而強調抽象的理論探索;而律師業則捨棄尊嚴,追求利潤至上。終而導致符合倫理規範的法律執業模式,被學術界和律師界同時放棄6。
學者將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的落差原因,歸納如下7:
一、歷史沿革的觀察:西方系統性的法學教育,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紀的古羅馬時代,當時貴族階級是在公開法庭聆聽學習並且接受法律專家的保護。而不願服侍貴族的優秀法學家就自己設立學堂,教授法律。但在古羅馬的法律實務工作者看來,這些法律教師只是「雄辯的雜技演員和法律的掠奪者8(acrobats of oratory and despoilers of the law)」而已,顯見當時司法實務對於學術研究的蔑視心態。
嗣後中世紀的歐洲,雖然法學院、醫學院和神學院成為大學的重要組成,但因律師始終服務權貴而遭鄙視,連帶地法學教育也被批評偏重實務操作而欠缺理論基礎。因此,為了與其他學科在校園內競爭,學術研究開始發展抽象的法學理論,避免被認為只是律師的技職教育。時至今日,學術研究仍然沿襲歷史脈絡,有意識地與司法實務保持距離,孤芳自賞。
二、經濟發展的分析:現代法律產業發展已將金錢報酬作為主要目標9,本質更像商業,因此會將選擇學術研究工作者錯誤地詮釋其欠缺商業競爭力,因而加劇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的鴻溝。
三、教育方式的改變:當代法學教育模式,偏好以模稜兩可、邊界地帶的爭議個案作為教材,教學重點在於贏得辯論,而未必是服膺法理,因此導致法律工具化的價值虛無主義10,也和倫理道德等原則無關11。
正確地認識法官和學者的功能歧異,其實應該作為認知角色侷限的自我警醒!因為法官不是全知全能,卻又承擔形塑國家公權力的責任,所以司法實務非常強調經驗累積的重要性。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 即在判決中援引制憲元勳的見解:「經驗是真理的神諭!當其回應明確,就是無可質疑而神聖的12(Experience is the oracle of truth;and where its responses are unequivocal, they ought to be conclusive and sacred.)」
正因為「經驗」重於「創意」的職業屬性,所以法官有別於學者,對於法律見解的變更非常謹慎,否則就會減損自身權威。這種本質上的限制,恰好說明判決理由為何向來保守?因為如果判決理由超出爭議範圍過度闡述,不僅減損公信力,而且未賦予其他利害關係人發言的機會,正當性即有可議13。
和學者的自由揮灑相較,無論法官個人的專業權威多麼崇高,除了自己心證確信之外,還必須「說服」同僚形成多數意見,否則也只是在評議程序中的一票。學術權威意見必須落實為合議庭多數見解,才能產生實益。相反地,判決理由附隨的協同意見或不同意見,卻反而彰顯學術研究的獨立性14。
從事司法實務的法官和致力學術研究的學者,明乎所以,清楚定位,更能協力促進法律發展。
[1] Charles Fried, Scholars and Judges:Reason and Power, Vol. 23 Iss. 3, Harvard Journal of Law & Public Policy, 807-832 (2000)
[3] Id. at 811-12
[4] Harry T. Edwards, The Growing Disjunction Between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, Vol. 91 No.1 Michigan Law Review, 34-78 (1992)
[5] Charles Fried, supra note 1, at 813
[6] Harry T. Edwards, supra note 4
[7] M Weir, The Dissonance Between Law Schoo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— the Why, the How, the Where to Now (1993) 9 Queensland U Tech LJ 143.
[8] Anton-Hermann Chroust, Legal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, Vol. 7, No. 4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509-529, at 515 (1955)
[9] Harry T. Edwards, supra note 4
[10] RC Cramton, The Ordinary Religion of the Law School Classroom, Vol. 29, No. 3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47-263, 254 (1978)
[11] JR Elkins, Moral Discourse and Legalism in Legal Education, Vol. 32, No. 1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11-52, 12 (1982)
[12] Printz v. United States, 521 U.S. 898 (1997)
[13] 例如報載若干判決在本案核心爭議之外,偶有感時抒懷、針砭時事等論述,其本質與英美法系所稱「判決傍論(dictum)」相去甚遠,值得商榷。
[14] Charles Fried, supra note 1, 826-27
- 發布日期:112-06-07
- 更新日期:112-06-16
- 發布單位:法官學院研究發展組
